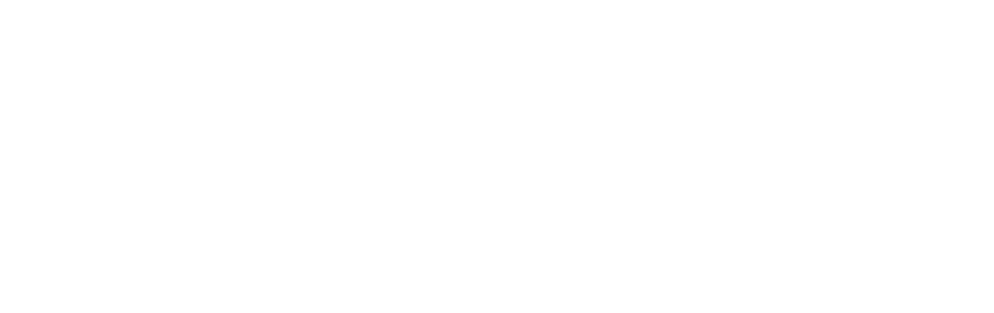犹记年少时曾略读过谷崎润一郎的《春琴抄》——一个性格古怪的盲人富家女,一个包容内敛的男仆,一段常人无法理解的畸形爱恋。
那时我觉得这样带有宗教色彩信仰的爱,只可能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。
直到那天,我也失去了我的眼睛。
这不是抽象的概念,只是简单的陈述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高度近视的我去换镜片的时候,发现右眼几乎失明。
小宇接到电话以后直接打车到了医院,我滴了散瞳药水,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发呆。小宇一会扒在门口看医生,一会又跑出去拿什么单子。
眼睛的损伤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,我看着模糊的世界,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一样。病房门口传出老太太的一声哀嚎,我想不通眼科怎么会有人哭天抢地。
不过,丢了一只眼睛,也确实该哭。
很久之前在圈子里见过一个小男孩,很可怜,天生好像得了什么病,发育不良,最多只能活到三十岁,四处找好心的女斯收留,希望能在快乐中结束生命。还遇到过一个喜欢用繁体字的男人,说自己是脑瘫(疾病)。他彬彬有礼,温和热情,把自己的情况挂在主页,基本得到的都是礼貌的拒绝和暗暗的疏远。还有一个圈里相识多年的老友,在查出癫痫以后退圈,很多时候连生活都没办法自理。
我的左眼九百度,我的右眼近乎失明。我忽然想起那本书,里面那个孤傲的春琴,还有她忠诚的佐助。
结果出来,是视网膜脱落,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
我父母赶到的时候,小宇还是不肯走。我很大力气掐了他一把,他说我这儿离不开人,他是我男朋友。
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我病了,他开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。
手术很成功,但也没有太大起色。我不敢哭,害怕恶化情况,也不愿意让小宇或者父母看到这样的窘迫。
在医院躺着的那些日子,我开始思考往后的人生。小宇还只是个小孩啊,想起进手术室前他还说,要一辈子跟着我。
我不需要别人为我刺瞎双眼,也没办法享受这样的爱。
在一起住的房子续租了一整年,水电交了不少,物业费也交了一整年。想了又想,我还是把那些道具都扔进了垃圾箱。我多付了些钱,让司机帮我把很重的行李箱合上,再提到楼下。父母在家里等我,术后需要静养。
那天回去的车上,手机一直一直在震动,是小宇的来电。我大概能想到他回家后的崩溃和难过,因为我也一样。情感让我留下,理智让我离开。
小宇在宽慰我的时候说,他最喜欢服侍我了,一直以来他都做得很好。像一件最合心意的玩具,又像一件最趁手的工具,他一直热衷于取悦我这件事。
但服侍和照顾,最大的区别是,一个是能自己做但是想让他去做,一个是没有能力去做只能让他去做。
我没觉得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在这个圈子苦苦追求有什么不好。有时候越是压抑越是残缺,就越会渴望极致的精神世界,尽管在我看来这很不负责。
我没有接电话,也没有通过他的微信。我不能流眼泪,只能木然听着窗外的车来车往。
再见,我热爱的圈子。
以及,亲爱的小宇。
佐助摸索着来到里屋,跪拜在春琴面前,以额头触地,说道:“师傅,我也已经是盲人了,这样一辈子也看不见您的脸了。”“佐助,这是真的吗?”春琴只说这么一句话,便陷入长久的漠然沉思。佐助有生以来,此前此后,从未感受过自己活在这几分钟沉默里的绝对快乐。——《春琴抄》
本文版权所有:绵花舍平台,转载请注明出处,侵权必究!:http://miansm.com/?p=1363